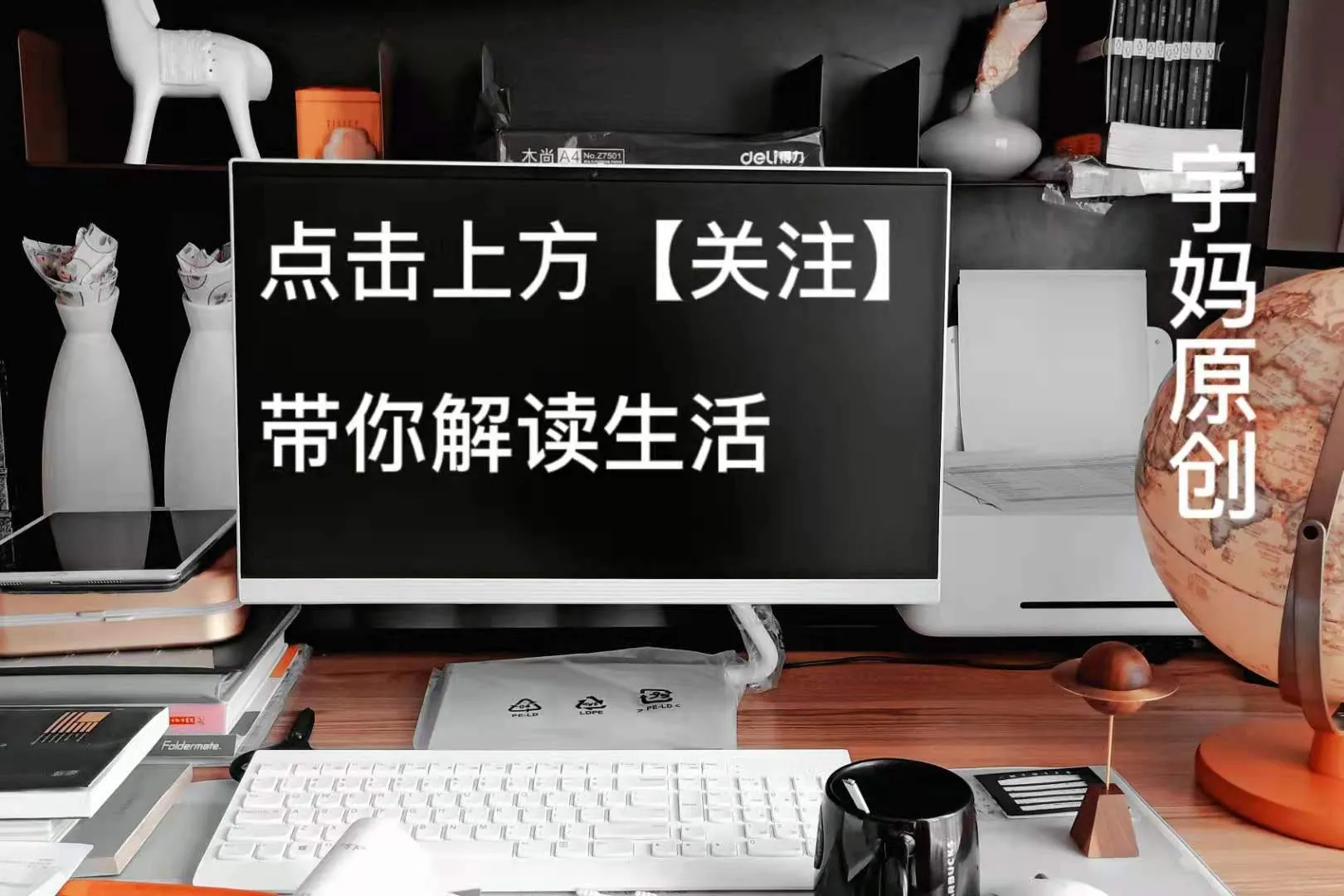
春寒料峭,街面上一片萧瑟,没有一点生机,警笛的鸣叫声打破了昔日矿区的宁静。
单身楼上,相对的两面窗户都打开了,是在家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想看看这热闹是从哪里来的。
一楼楼梯口聚集着不少的人,对着警车指指点点。
周文斌在乔姨家打牌,都还以为是查抄室的,因为几个警察去了室。
乔姨陪着笑脸说:“大家都是无聊玩玩,没有,真的!”
桌面上没有钱是真的,输赢都是发的纸牌,就是为了防范查抄的警察!
三个警察进屋里巡视了一圈,一个年纪大点的警察说:“玩儿玩儿可以,禁止钱啊!谁是周文斌?”
背对门口坐着的周文斌心下一惊,迟疑着举起了手“我是。”
警察说:“跟我们回所里一趟吧!”
他一摆手说:“带走!”
周文斌慌忙站起来,语无伦次地说:“不是,警察同志,我怎么了?我遵纪守法没犯错啊?打麻将要抓起来啊?和别人的老婆睡觉是犯法的啊?”
他一番话把警察都给整懵了,其中一个警察说:“啥乱七八糟的啊?就是例行询问,没啥事儿,别怕,都别围着了,干啥呢?看热闹到别的地方去啊!散了散了!”
周文斌跟在警察后面,一边下楼还一边说:“警察同志,我是好人,真没犯事儿,到底啥事儿啊你们抓我?”
警察不理他,对着楼道口的人群说:“散了散了啊,该干啥干啥去!”
周文斌被带上了车,就像是犯人一样,他和两个警察坐在警车的后面,窗户都是铁栏杆,他的心里更怵了!
他一脸慌张地喊:“警察同志!”
两个警察眼观鼻,鼻观心,没有回答的意思,他索性闭了嘴。
派出所并不远,很快就到了,只是这阵仗有点大,只差给她带个手铐了!
他一个人坐在审讯室里等待,尽管他是混蛋,可还不至于犯罪,他没那个胆子,派出所啊,做梦都梦不到的地方。
活这几十年,他除了办身份证,还真没来过这个地方。
时间漫长,那个带他回来的老警察,拿着文件夹和一支笔坐在了他的面前。
周文斌迫切地看着他,他动了动桌子上的杯子,把钢笔冒取下来,盖在笔杆上,然后,在文件夹上,写上了日期,抬头看着他“说说吧!”
周文斌一脸迷蒙地说:“说,说啥?”
警察说:“姓名,年龄,职业。”
周文斌老老实实地回答,警察拿出来一张照片问:“认识她吗?”
周文斌仔细看了看说:“见过。”
不能说不认识,也不算认识,只能是见过!
那是一个看起来很奇怪的女人,两只眼睛不对称,脸蛋浮肿,眼神呆滞,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粉色上衣,裤脚一个长,一个短,她很年轻,应该说她年纪很小,她不是正常人。
不能说不认识,因为他经常见到她,不光他,矿上就没有人没见过她。
她是附近村上的,是个智障孩子,整天脏兮兮的在街面上逛,大多数时候衣不蔽体,小孩子看见她都躲得远远的。
她一天天长大,有智障孩子的特征,也有正常女人的特征,她长大了,就更明显了。
有时候她生理期,屁股后面一片红,有心软的女人给她穿过衣服,她还是给脱扔了,饿了就扒垃圾,困了随地就睡了。
她是有家人的,不知道是管不住,还是无暇管,总之终日在矿区市场居民区一带游荡着,慢慢地长成了女人。
她怎么了呢?周文斌一头雾水,一点头绪都没有。
警察说:“这个女孩儿叫王梨,她怀孕了,有人举报看见你跟她在一起过,她家人现在要告你。”
周文斌着急地说:“不是我,怎么可能是我呢?我也不缺女人,再说她还那样儿,警官,真不是我。”
警察说:“是不是你,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去年的十一月六号,你在哪儿?做什么?有没有证人?”
周文斌更懵了,十一月六号,他费力地想着,想不起来,几个月过去了,他能做什么?除了打牌,出租屋,就是室。
他摇了摇头,警察说:“我提醒你一下,十一月六号傍晚,你和王梨在一起。”
周文斌急忙说:“不可能,我怎么会跟她在一起呢?我除了在街上见过疯疯癫癫的她,在别的地方根本没见过她。”
警察说:“有人看见你十一月六号傍晚和王梨在二号单身楼后面的胡同里侵犯了她,导致了她怀有身孕,现在,家属要告你强奸,你最好有证据证明那不是你。”
周文斌说不上来,也没有证据,他自己都记不清楚时间,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在干什么?怎么找人证明自己做什么了?
他十分绝望,他不停地说:“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没有跟她在一起过,没有强奸她。”
警察把手里的笔轻轻地敲在桌子上,一下,两下,三下,就像是敲在他的心上一样。
他什么也提供不了,警察进行完例行的盘问后,由另外的警察带他去抽了血,并且告知他不允许离开本市。
他没有家属,只有自己,警察局通知了单位,他的队长来把他领走了。
本来平时他就不怎么上班,经常游离在被开除的边缘,这一下子,他队长是一点好脸色都没有。
公事公办又戏谑地告诉他,如果他犯法了,拘留那一天就是被开除的那一天。
一时间这件事情就像是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矿区的每一个角落。
只是接受调查的他,不过半天功夫,就成了强奸傻子的强奸犯。
别人不知道他是谁,室里的常客都知道了,就连平时一起玩的人也都对他指指点点,那个女孩儿真的肚子大了起来,他从派出所回来的那一天,还见过她。
这真的是飞来横祸,对他来说,这莫须有的事让他寸步难行,室也不去了,班也没办法上,整天待在家里等。
陈朵儿也知道了这事儿,她心里很着急,她是相信周文斌不会做这事儿的,可是,为什么会攀上他呢?
白永强幸灾乐祸,他翘着二郎腿,叼着烟,哼着小曲,晚饭后他对陈朵儿说:“臭娘们儿,你是真能耐啊!看上一个强奸犯,你是不是本来就知道他是个强奸犯啊?”
陈朵儿不理她,一点点把地板拖干净,洗衣服,收拾床准备睡觉,白永强夜班,他站在卧室门口看陈朵儿收拾床,心里就窜起一股无名火。
他走过去,站在陈朵儿的背后说:“咋?说你的老情人你不高兴啊,妈的,赶紧把他抓进去,最好判个死刑!”
陈朵儿放下手里的被子,转过身,她和白永强脸对脸几乎贴在一起,她说:“是不是你举报的?你真的看见了?”
白永强说:“警察也不是吃干饭的,我没那么闲,咋啦?你心疼了?哎?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个事儿,你是不是也被他强奸的啊?你一句话,老子也告他去,不把他驴熊抓进去我不姓白。”
陈朵儿看他一副无赖样儿,她觉得最近真是重新一点点认识了白永强一样。
她脱了衣服上床,白永强也脱了衣服上床,陈朵儿说:“你不是该上班了?”
白永强伸手关了灯,一把把她按进被窝里说:“你是不是又想偷人了?真是贱,不去了,睡觉。”
陈朵儿说:“你最近老是这样不上班,你们队长也不说你?”
白永强说:“老子想上就上,不想上就不上,谁能管住我?咋啦?是不是耽误你偷人了?”
他话里话外地怼陈朵儿,句句带刺,陈朵儿索性闭了嘴,转过了身。
白永强一把把她扳过来,双手抓住了她的胸,陈朵儿疼得鼻子发酸,她咬牙忍着。
忍着吧,忍忍就过去了!
陈朵儿上班的时候打电话给周文斌,两人约好,她请假和他一起去了市里。
多日不见,陈朵儿满是柔情,周文斌满心满眼的委屈,毕竟这么多年了,他也不是没有一点心,一个人孤独无依的时候,他还是会想她的。
两个人苦兮兮地缠绵了一回,周文斌说:“那个啥玩意儿?说是我给搞怀孕了,我他妈的招谁了?就招姓白的了,要真是他搞我,我非跟他拼命不可。”
陈朵儿说:“我问过了,不是他,他没有,警察咋说的?”
周文斌说:“那个智障流产了,我抽了血,说是比对DNA,妈的,真是冤枉死我了,他说不是他就不是他啊,你那么相信他?绝对是他没跑儿,我要杀了他!”
陈朵儿知道他胆小怕事,过过嘴瘾而已,也不再辩驳什么。
周文斌说:“这事儿不是我做的,闹这么大,人也丢了,工作也快丢了。”
陈朵儿爱心泛滥地说:“不是还有我吗?饿不着!”
周文斌眉开眼笑,陈朵儿看他没啥事儿,也放心了许多。
下班时间,陈朵儿回到了家,一进家门,白永强拽住她的头发,把她推搡在沙发上说:“说!是不是跟野男人睡去了?”
陈朵儿说:“你发啥疯,我上一天班你不知道啊?”
白永强一巴掌扇在她脸上说:“上一天班?我看看你嘴有多硬?”
陈朵儿的双颊发烫,头发披散在脸上,分外狼狈。
白永强说:“你那么浪吗?我要是昨天晚上上班,是不是又滚我床上去了,我跟你说陈朵儿,你别逼我,把我逼急了,我把你们两个一起剁碎喂狗!”
陈朵儿抬起头说:“我没有,我去看珍珍了!不信你问她,白永强,我们离婚吧!”
白永强一屁股坐在她身边,一只手攥住她后脑勺的头发,让她把头抬起来看着他说:“离婚?好啊,打电话让燕燕和陈涛也离婚,当初一起办的,现在离婚也一起办!”
陈朵儿突然笑了,她笑完闭上了眼睛,白永强说:“你趁早死了这条心吧,我打死你都不会跟你离婚,还有,你最好安分一点,要不然,不是我坐牢,就是你的野男人坐牢,好好想想吧!”
白永强走了,陈朵儿像是被抽空了一样,瘫软在沙发上。
夜幕降临,黑暗一点点侵袭了这片黑色的大地,白永强像一只捕食的鬣狗一样蹲在楼角的暗影里。
他抬头看着二楼的一扇窗,那里亮着灯,他的屁股下面坐着一块红砖,那是他从市场上一处工地捡过来的。
他一直在那里蹲守到了十一点钟,楼上的灯已经熄灭半个小时了,他没有等到他想等的人。
白永强站了起来,活动了一下发麻的双脚,又抬头看了看那扇窗,踉跄地离开了破旧的小区。
天上残月如勾,夜幕下形单影只,他似乎又闻到了令人作呕的血腥味!
待续!
每日早晨六点更新连载:观看1-23在主页!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点赞,评论,转发
愿读故事的您,天黑有灯,下雨有伞!

 十大足球直播推荐
十大足球直播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