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曾经送别挚爱之人离去时的悲伤,仿佛又重新回到了心头。悲伤是人类无法逃避的情绪,而寻找爱的寄托,是我们每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治愈自己的方式。
深读142期,我们来看一个古怪老头阿方索的故事。他和妻子诺莉亚一直没有小孩,终于在某一天,诺莉亚决定去领养两个“重生娃娃”——一种手工制作的娃娃——当做自己的孩子,并叫她们“姑娘们”。
曾经,阿方索对妻子有着各种的“不满”:带着“姑娘们”上街,哄着“姑娘们”入睡,给“姑娘们”掖被子……而如今,阿方索自己却做起了这些事情,变成了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而这,正是他排解悲伤的方式。

玛利亚出生的时候,诺莉亚和我正在当地泡吧。我们在酒吧里一杯接一杯地喝啤酒,啤酒味道很浓郁,感觉就像喝着一杯杯鲜味汤。我们嘲笑着自己,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但领养当天我们非常严肃。我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只有在离家千里的地方才会产生的、自由解脱的感觉。我下定决心,要充分理解我老婆,并且享受这一切,就算只是为了让诺莉亚开心。梅丽莎(玛丽莎)拿着一个有透明塑料盖子的盒子,把玛利亚呈给我们。
不管你看多少莎士比亚,去多少艺廊展览,都不可能预想得到眼前的这种高度写实主义。所以很多人不喜欢高度写实主义,完全不认为那是艺术: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种装腔作势、骄傲自满的风格,总能考验你的心智与感官。我们可以叫她姑娘、娃娃……想叫什么都可以,但玛利亚的样子完全就是个刚出生的婴儿,正如我就是个风烛残年的老头。我们“呜哇”乱叫地打开盒子,然后打开一瓶给重生者带的常温香槟,轮流去抱玛利亚。我们学会了给她穿衣服,给她洗澡,以及给她换电池。
……
诺莉亚和梅丽莎(玛丽莎)熬了夜,一直到凌晨才睡。她们喝茶又喝酒,和娃娃一起玩耍。天知道她们到底喝了多少。我只知道,当我醒来的时候,(1)各种各样的重生娃娃穿着传统的墨西哥节日盛装;(2)诺莉亚又买了一个娃娃。我当时急着逃离那个地方,没心思跟她争,而且钱也全是她出的,所以我闭着嘴什么也没说。
和我认识的其他所有医生一样,诺莉亚自己是不看医生的。这是属于这些专科医生的倔强,他们觉得自己三十年前掌握的那些粗浅的全科知识能帮他们挡住一切病痛。诺莉亚总是自己进行病况评估、自我诊断、自我开药治疗,而且,还会在只瞥一眼的情况下,就对我进行病况评估、诊断和开药。只要那病跟心脏无关,她的诊断经常不准。当然,她对自己的误诊结果要糟糕很多,但至少有一次,她也把我折腾得够呛。应该是在1987年左右吧,我还记得当时小院的建设工程进行到一半,还没有“姑娘们”。某个周五,我突然觉得非常非常不舒服,诺莉亚立刻让我吃了扑热息痛,喝了热茶,一直到周一。等周二我醒来时,双眼已经变黄了。我那是得了严重的急性肝炎,最后侥幸活下来,多亏了当时立刻去医院,他们给我打上点滴,输了各种各样的药。而她自己就是拖了太久才去检查自己疼痛的地方。我之前还猜,一定是她的身体在抗议她对工作的那种无可救药的狂热。但等她终于去做检查的时候,身体里的癌症已经没法治了。
……

△ 《良医》
诺莉亚决定做化疗,不是因为她觉得会有效,而是因为她不想成日里无事可做。好在,她也同意吃大量的抗抑郁药,让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过得还算平和。他们也给我开了同样的药。我到现在还在吃。快要吃完了,我就从书房找出还印着她的名字和各种药品细节的处方单,自己开一张。我会伪造她的签名,这是婚后学会的本领,那时候我只是个初级研究员,也没有租金收入,所以我们的生活开销全靠她的信用卡。
最近我把药量加倍了,告诉自己是在为我们两人吃。
我不喜欢那个得肝炎的故事,特别不喜欢诺莉亚当众讲。故事里面的我既没有男子气概,又没什么主见。我感觉这事证明了她对我想干吗就干吗,而我就乖乖任凭她摆布,既软弱又顺从。我那时候没有,现在也不会否认自己是个怕老婆的人,也总是公开承认,而且理直气壮一点也不觉得丢脸。但我觉得我做出牺牲的种种细节我俩知道就好了。我觉得得肝炎那个故事是特别私密的故事,每当在晚餐聚会上不得不听时,我总有种受到公开侮辱的感觉,就好像诺莉亚在对座上各位讲我们初次见面时,我被抱着就睡不着觉,但现在却是不抱着就睡不着。同时我还“皈依”了“拥抱教”“周日穿宽松运动长裤教”,甚至“冻鱼教”(尽管知道这样会让维多利亚湖慢慢枯竭)。她甚至还说服我时不时地陪她看看浪漫轻喜剧。现在呢,为了入眠,我必须得在背后支两个枕头。但等我上了卫生间再躺回来,枕头不会拥抱我,也不会温暖我。上床之前我会对肯尼和G唱歌,给她们掖好被角。自从我们把她们带回墨西哥,诺莉亚每晚都要做这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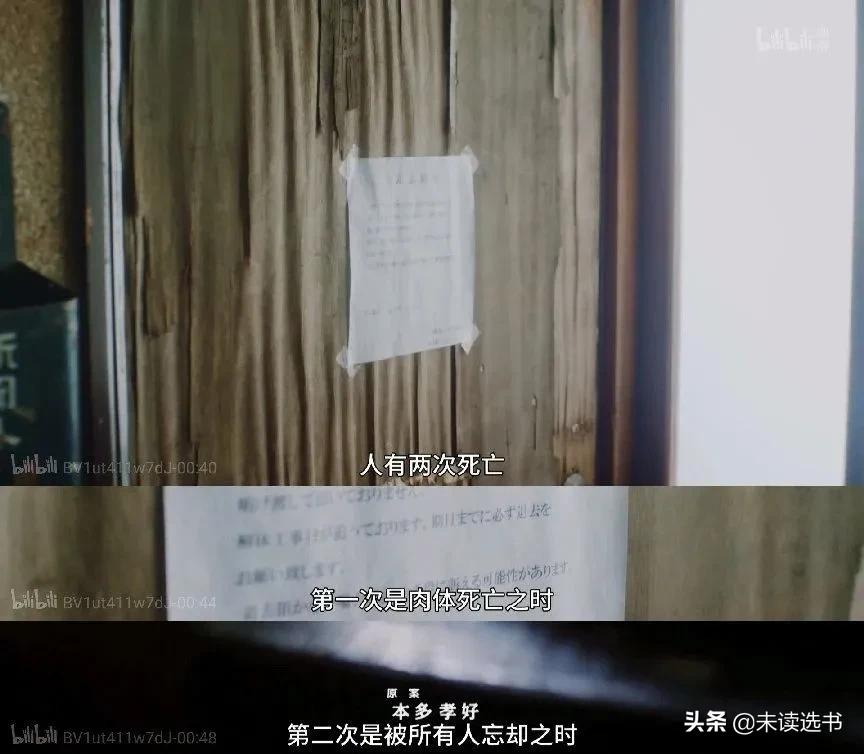
△ 《人生删除事务所》
诺莉亚在晚餐聚会上绝口不提的一件事,就是“姑娘们”。以前我很感激她的沉默,现在我有点后悔。或者说,我不后悔,但我变了。从前,要是诺莉亚把“姑娘们”带到街上,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要到处跑来跑去确保邻居们不会看到我们推着推车走过。现在我真是一点也不在乎。我不在乎大家都觉得我是这一片的疯老头。几个月前,我开始带着“姑娘们”满院子走,要是有人感兴趣,就跟他们解释说,她们确实只是娃娃,不过是特殊的娃娃。结果,真正的小姑娘可喜欢我的“姑娘们”了。晚上,我把她们放在推车里出去转一圈,还快乐地吹着口哨。我还是不敢把她们带出小院,到大街上,但我计划很久了。
“你推她们出去走会很性感的!就像那种性感老爷爷。”
“你还真是爱花言巧语呢,亲爱的,谢啦。”
“带她们出去,对你有好处的。”
“我试试吧。”

我们没有孩子的人生,既不大,也不小。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尺寸来形容,就是正常。“姑娘们”来了以后,打开了一个我们之前没有的新世界。卧室里摆满了粉嫩甜美的小饰品、小玩意儿,正常来说我是很讨厌这些的。但说句实话,最近我进到那个房间,看到荷叶边啊、蕾丝花边什么的,感觉真好。我算是理解了吧。或者也许只是终于看清了。此生只有诺莉亚·瓦加斯·瓦加斯看得透我。现在呢,我根本无从得知,到底我有多大一部分是只存在于她的凝视中的。
诺莉亚患了癌症以后,我才开始觉得这些娃娃不只是娃娃,而是“姑娘们”。多年来我都支持诺莉亚去做那些异想天开的事情,但在心里还是保持着自己的距离,算是一种保护性的讽刺吧。诺莉亚想把楼上的房间给她们,我接受了。她想在墙上贴淡粉色和淡灰黄色相间的进口墙纸,我问自己,如果是她付钱,我有什么好吵的呢?她买了婴儿座椅,开始把“姑娘们”放在车后座上跟我们一起出行,我告诉自己,不要绝望,这只会让你更坚强。现在回望过去,随着“姑娘们”而来的大起大落的情绪,其实就像为我们本来已经对大多数事情习以为常的婚姻注入了青春的兴奋剂。有时候我为诺莉亚难堪,有时候又为她骄傲。有些时候感觉她这种小游戏很有趣,但有时候看到她在家里推着宝宝转圈,又让我心碎。这宝宝不是真的宝宝,也不是我的宝宝。

△ 《假如猫从世界上消失了》
有一次,一位警官砸碎了我们的车窗,因为诺莉亚到银行办事,把“姑娘们”留在后座上了。警官以为自己做了英雄,之后诺莉亚只得偷偷给他塞了一点钱,疏导他因为救了两个假人而产生的怨恨。我一直觉得,自己这个很棒的老婆对“姑娘们”的照顾,算是她的小怪癖之一。不过也可能就是荷尔蒙上头一时冲动。似乎她在子宫中感觉到一种很独特的疼痛,这种疼痛又有外在的展现。当然了,瓦加斯·瓦加斯医生说出了一种与症状相符的病(一半是意大利语,一半是拉丁语),可以解释母亲和孩子一同经过时,“只是个女儿”的人感觉到的痛苦:子宫缺失。
这一切真是特别诡异,但也没什么害处。人们投来奇怪的目光时,我当然也会有点生气,产生一种兽性的冲动,想去咬住别人的咽喉什么的。我觉不觉得重生娃娃这事奇怪呢?当然觉得啦!但这又没伤害到谁,还让她更开心了。我可是占据了最有利的观察位置。在我看来,诺莉亚出现“子宫缺失”的症状太晚了点,这可能是个遗憾。但这症状把她彻底击碎了,而她找到了一些途径来消解自己感觉到的消沉,嗯,这恰恰可以说是一点也不奇怪,对吧?那是各种各样的母性冲动:她照顾“姑娘们”,其实就是在照顾自己。她自我掌控,认清了让她伤心的原因,然后找到走出悲伤的最佳缓和剂。从没有孩子的状态中走出来,变成熟(而那些只是个孩子的人不是很少能达到这种境界吗),这难道不是为自己负责吗?不过,要是我想祝贺诺莉亚做到了这样的事情,她总是回答:“医生嘛,对吧?只不过想对症治疗而已!”

写到这里我要报告一条新闻:今天我带“姑娘们”去芥末屋了。还真是费了好大一番功夫。首先,他们说我带着“孙女儿”,不想放我进去。我解释说,她们都是玩具娃娃,结果他们不信。整个厨房的人(一共两个)都出来了,分别确认她们不是真的小孩,之后酒保才信了我。接着他以为我是要去酒吧卖掉她们,又闹了起来。最后我只能用诛心那一套,提醒他我对芥末屋有多么喜欢多么忠诚。一番奚落和道歉之后,他们终于让我进去了。我一直走到常坐的那张桌子边,肾上腺素才停止飙升。我感觉到骨子里的疼痛。浑身燥热,心烦意乱,满脸涨红。我急急地喝酒,每喝一口就越来越看清我推着车走进来的那一刻别人眼中的自己:一个荒唐可笑的老头。
但接着琳达来了,就仿佛这世界上最自然而然的事情一样,我抱起一个“姑娘”,她抱起另一个。我们把她们抱在怀里聊天。接着我浑身充满了一种全新的快乐,甚至可以用“得意”来形容。
“这是我的权利,”我想说,“寻找爱的寄托是我一个老光棍儿的权利。这爱的寄托不是别的什么人,而是不会死去的东西。”
……

△ 《人生删除事务所》
苋米,这种我为之失去理智的植物,味道淡淡的。不但“无鲜”,而且“无味”。自欺欺人有着巨大的能量,这是毋庸置疑的。我的味觉一直挺细致的,怎么会一直以来只看到鼻子底下的东西呢?也许你必须到了我这个年纪,才能看清生活的真相,看见你为之奉献一生、倾注所有精力的东西中其实包含着小小的讽刺。然后,你就得好好估量一下:这种荒谬到底多长、多宽、多高。但最后你还是只能哈哈大笑了之。对此生的一切你都只能哈哈大笑了之。
“那是我说的话呀,讨厌!”
“诺莉亚,你来了,我真高兴。我想你了。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洗耳恭听。”
“‘姑娘们’和我今天要在院子里干些活儿。农地已经没戏了,苋米反正也没什么味道,这气候也种不出木瓜,所以我会把你一直想要的那个‘极可意’安上。”
“哇哇,阿方索,你不知道我有多羡慕嫉妒!”
“你在那边没有极可意浴缸吗?”
“没有。不过跟你说件高兴的事,我们都是全裸着身子到处走。”
本文摘录自《生命的滋味》,有删节, 莱娅 · 胡芙蕾莎 著,何雨珈 译,2019年12月由未读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墨西哥城一个小院
五套以味觉命名的出租屋
酸、甜、苦、咸、鲜,里面住着四户人家
终日与人偶为伴的人类学家
抑郁又厌食的艺术家
被歧视的亚洲少女
以及妹妹去世的12岁姐姐
当代拉美文学的潜力新星炫目之作
生命的滋味 ¥23.8 购买聊 几 句
悲伤来袭时,你会如何度过?
评论区一起聊聊吧~

 十大足球直播推荐
十大足球直播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