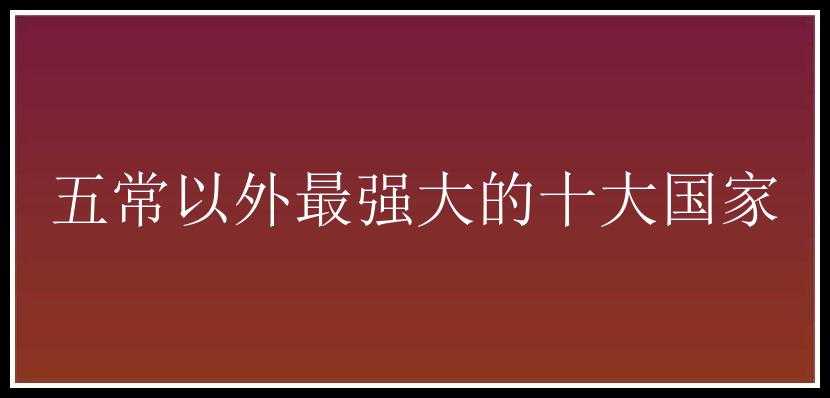在共和国的日历上,有着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段,在共和国的史册里,有着这样一页非常的记载,在共和国国度里,有着这样特别的一个群体,这就是工农兵上大学和工农兵学员。这个词汇在共和国的辞典中,虽然一闪即逝,却在1972年至1976年间,成为教育事业的创举。
我有幸成为工农兵上大学的一名学员,一名历史经历见证者。同时,也是因为有了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才改变一生的命运。
我上学的学校,当时叫黑龙江机械制造学校,座落在哈尔滨市南岗区学府路上,现已经更名为黑龙江职业学院。
这座学校,当时归黑龙江省机械工业厅管,以前学制是四年。我们入学的时候,学制改为两年。
现在感觉,虽然当时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和方法,教学质量和成果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从推荐和审查学员的机制和标准是相当严肃和严格的。学生们除了文化水平和基本素质不同外,政治条件和政治表现要求是绝对严格和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年能够在众多的竟争者中脱颖而出的,都是经历了层层推荐,审查和考核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的。特别是那些兵团农场知识青年集中扎堆的地方,名额指数特别有限,其竞争激烈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凡是实现大学梦想的学员,都是这个群体和团队中数一数二,出类拔萃的佼佼者。能够走进大学校门的都是在生产劳动和政治活动中取得成绩,表现突出的贡献者。
我们班有学员41人,其中女生10人,学习的是铸造专业。现在,我还能够记得当时的一首歌叫《工农兵学员之歌》:“迎着灿烂的阳光, 肩负党和人民的希望, 我们工农兵学员, 来自祖国四面八方。 带着工人阶级的委托, 带着贫下中农的期望, 带着革命部队......”
我第一次进省城哈尔滨,在哈尔滨站一下火车,就被锣鼓喧天的场面所震撼,学校的学生打着红旗在列队欢迎我们。先报到的同学,帮我们扛行李,一面往长春解放牌敞篷汽车上装,一面介绍学校的有关情况,问寒问暖,温暖如兄弟姐妹。
第一天报到,认识的第一个同学是五常县的葛德武,他也是农村大队保送来的。看他有些驼背的腰,黑红色的脸庞,粗皱纹的手,跟我一样差不多身着穿戴,肯定前些天还在生产队干农活。在学校食堂吃饭,需要自己带碗筷等餐具,从家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些,我们就一起搭伴到和兴路的商店去买碗筷和其它日用品。
农村孩子来到大城市,一切都感觉新鲜好奇,懵头转向。好在,我们两个人谁都不笑话谁。也是从这天开始,我知道了,那油漆马路上跑的车,车顶上有两个大辫子的绿皮汽车叫无轨电车;那个形状像长方形面包,在铁轨上两头都能开得叫有轨摩电;这里的楼真高,看上面人家的窗户累眼睛;人也多,道更宽,没有“土拉咔”,更没有马粪蛋子。
和兴路百货商店现在已经看不上眼了,可是在当年,虽然只是两层楼,看得我俩却是眼花缭乱,比我们村的供销社强上一万倍之多。我俩都知道自己兜里有多少钱,都选最贱的碗和小勺子买。然后,没有舍得花五分钱坐公交车,从和兴路一直走到学校。
这里需要多说几句,就是这个葛德武同学,毕业后分配到五常市农机局工作,任农机局副局长兼农机公司总经理。这个公司多年一直是省市的先进集体。在刚刚推行企业改制中,他积极推进改革,公司职工大量下岗。他让“职工没饭吃,职工让他不吃饭”,被下岗职工的孩子活活杀害在家中。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同学中间是墓碑》的文章,发表在刊物和网站上,引起很大反响。
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真说不清楚,我做梦都没有想到,开学第一天,班主任老师宣布我为班级的学习委员。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的文化水平,也不知道班里同学都是什么学历,不知道啥叫“藏龙卧虎”,还感觉挺高兴,当上班级干部,是很非常光荣的事。
我们这批工农兵学员的年龄差距很大,最大相差将近十岁,有的人曾在大队担任过村党支部书记,上学就是为了成为国家干部挣工资。在文化基础上,更是参差不齐,基础好的是老高二和高三毕业生,低的是在戴帽中学学习的。现在有人总结当年我们这批学生是“大学的文凭,中学的水平,小学的基础”。这对当时相当一部分工农兵大学生来说是真实的写照。
其实,我就是戴帽高中毕业的所谓的“高中生”。进了学校门,我这个乡下的“井底之蛙”,才知道井外的天有多大。我们班级高三同学很多,特别是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地同学,更是“人精”,他们懂得的知识比老师都多,在学习上更是呱呱叫。我这个学习委员别说去辅导别的同学,自己学习都感觉吃力,唯一自慰的是语文成绩很好,写作文老师总是表扬,学校的黑板报经常刊发我的文章,各种运动会,文艺演出都是我写的解说词。但是,我们是工科学校,语文只是一个副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想,我真不应该来这个学校,我应该是写文章的人,不是干技术的料。转而又一想,不来这个学校,我就还是庄稼人,还是在“脸朝黑土背朝天”干活。别胡思乱想了,好好学习吧,有了工作,以后再想办法转行做自己喜欢的事。
是啊!年轻人,就是好幻想。

 十大足球直播推荐
十大足球直播推荐